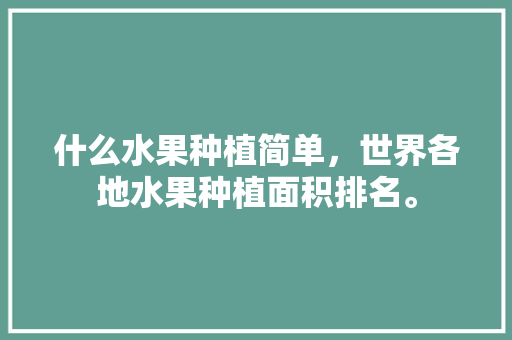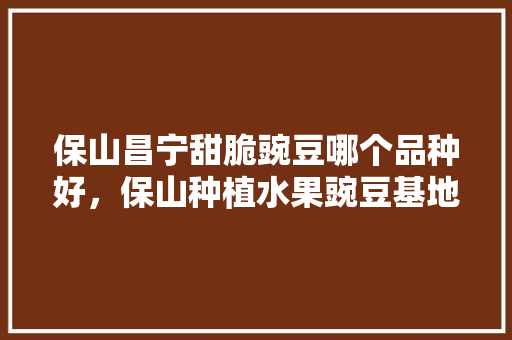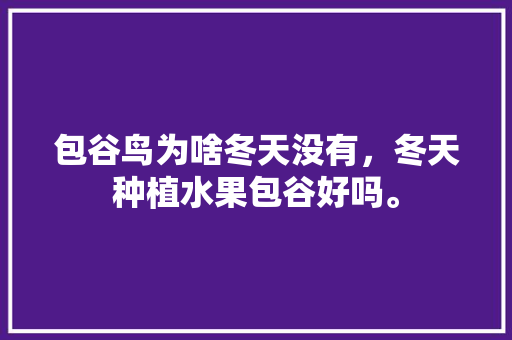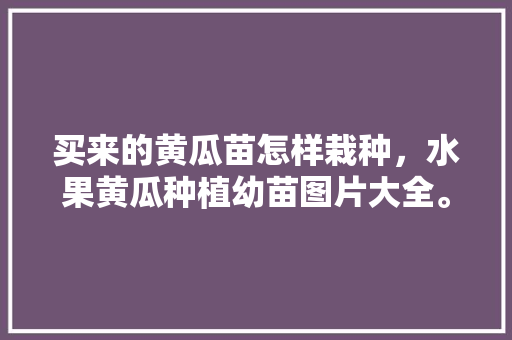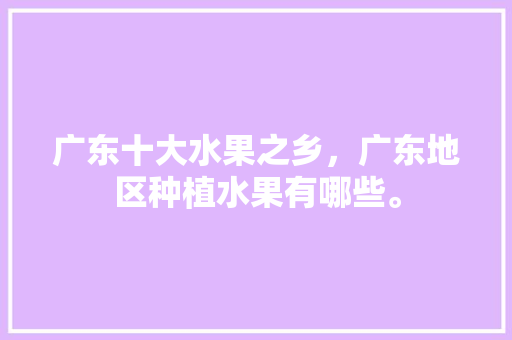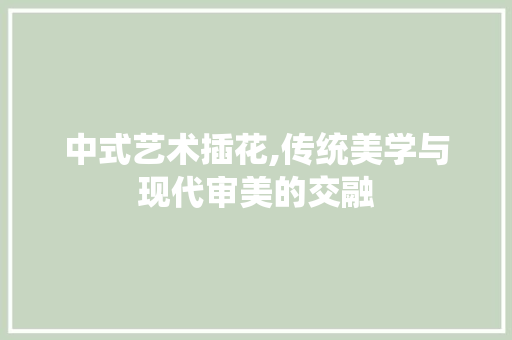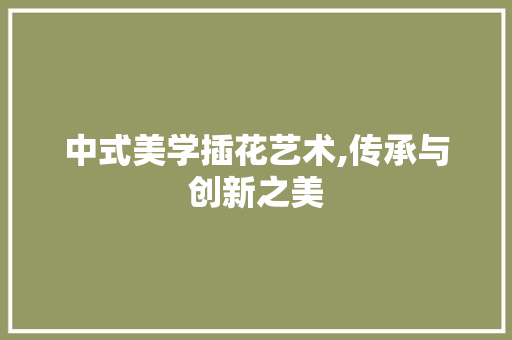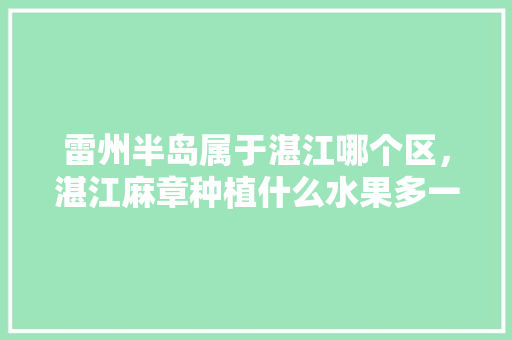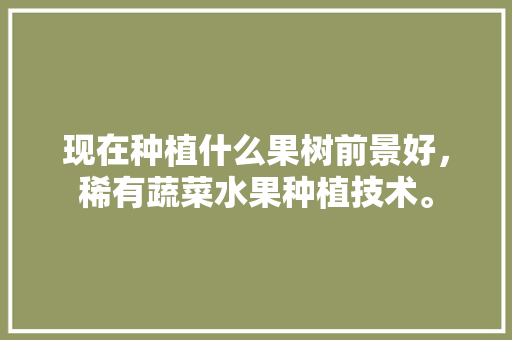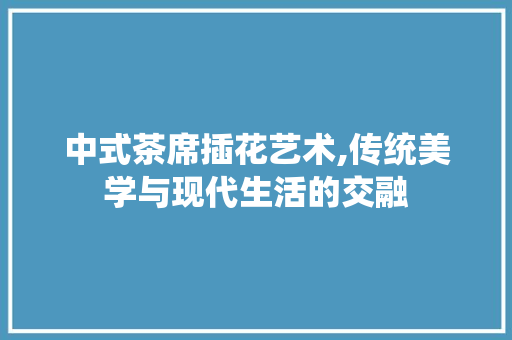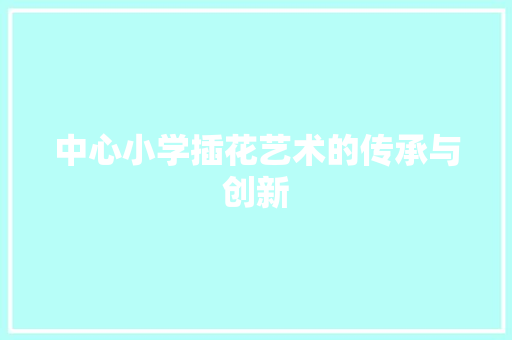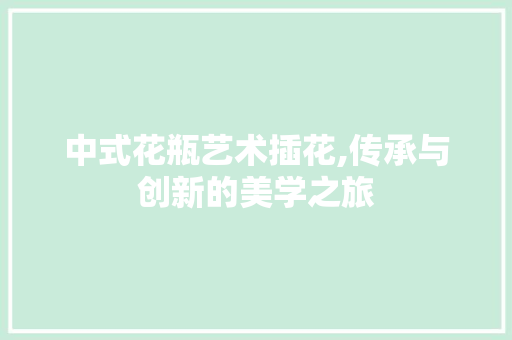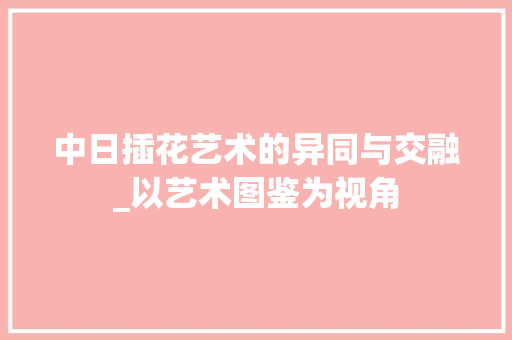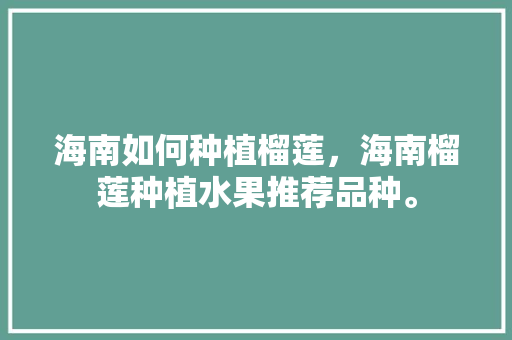东北晒干菜过夏季能吃吗
东北人晒干菜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了,每年秋季菜便宜时都会选择太阳好的天气晒一些干菜:芸豆、土豆、茄子、青椒……冬天青菜贵吃它不仅便宜,还别具风味。但干菜的收藏要注意通风,伏天特别容易发霉长虫子,长虫的干菜就不要吃了,如果没生虫的干菜过了夏季仍然可以吃。
传世经典《诗经》要怎样读
读诗经,不要把诗经当成什么经典文学名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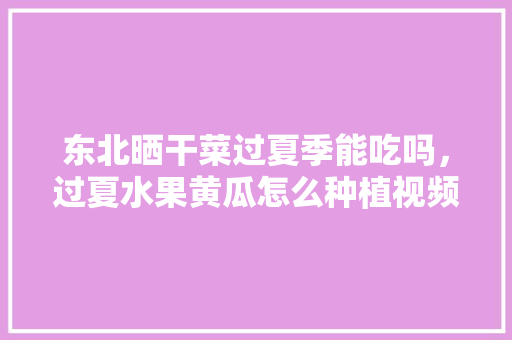
甚至不要当成诗歌。

你可以把他当成一部古代人生活的记录来看。你会发现,古人跟咱们一样。
这里面有羔裘五陀的朝廷大员,有夙夜在公的基层小吏,有劳碌的宫女,有新婚燕尔的少女,有错嫁的怨妇,有在家思夫的少妇,有终年在外的戍卒,有坎坎伐檀德工人,有一发五豝的猎手……,这里面有伤心有得意,有羡慕有赞颂,有自责有悔恨,有誓言有赌咒,有暗恋有表白……总之,一部诗经,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老祖宗真是丰富多彩,这也是为什么诗经里“风”比“颂”好的原因。
如果这个不过瘾的话,你把诗经当成侦探小说来读。
为什么呢?
因为啊诗经从孔老夫夫子开始就广受关注,汉朝还有专门的机构研究,历朝历代都对之孜孜以求,但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有些事情就是被专家搞乱了,诗经被这些专家解释的乌七八糟,总之阿狗说阿狗的理,阿猫说阿猫的理(李敖的话)。
有时候这些专家注解得虽然你觉得狗屁不通,但把他当故事,你从中找出中最有趣的来。
我一直以为朱熹老先生注释的诗经都是君王仁义,理性人心什么乱七八糟的,比如把什么关关雎鸠说成宫女咏大姒文王,但一番看下来却发现朱熹老先生有时候见解很独到的,比如有些情诗方玉润孔颖达解释为君王妃子什么的,但是老先生就不一样,他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淫诗,淫女在思夫什么的,虽然在还是持着批判的态度,但也基本上肯定了诗歌的性质,不过在他的眼里,情诗就是淫荡的表现而已。
锦翼系悟空问答签约作者
谢谢邀请。这个问题颇有意思。下面说说我的看法,仅供诗经爱好者参考,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谈谈您对学习《诗经》的方法和经验。
首先,了解诗经产生的时代背景。我们都知道,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,作品产生的年代从西周初年(约公元前11世纪)到春秋中叶(约公元前7世纪),时间跨度长达4百年,收录的305首诗歌堪称经典之作,几千年不衰。可以说,它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之作。阅读诗经,应当了解其作者、产生的时代、内容以及它的来源、背景,这是非常必要的,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
其次,阅读《诗经》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。我们通常说的“诗言志”,我个人理解是,古代人所谓的“言志”,其实就是政治或教化的体现,“诗”就是“言”和“志”的综合体。从这个层面理解,我认为“诗言志”就好比今天的点歌,完全可以“断章取义”。比如,用歌颂邂逅爱情之歌来表达对远道而来的国宾的欢迎之情。
第三,掌握《诗经》的核心要义,极其重点非常重要。比如,《诗经》的“六艺”(风雅颂赋比兴),所谓风,就是要知道它共有15国风160首诗,这些诗都属于民间歌谣,歌唱男女恋情和各地风土人情的。再比如雅,诗经中分为大雅和小雅,共有15个乐章,都是适用于宴会和寺庙的乐章。颂,主要包括《周颂》和《商颂》、《鲁颂》,主要是用于敬天祭祖的乐章。“赋”:就是叙述和描写,用直接叙述或描写某一件事。“比”:就是比喻,《诗经》当中运用非常广泛,主要包括明喻、暗喻、隐喻和借喻等等。再说“兴”,就是启发的意思,也叫做起兴,就是说诗人见到某一事物触动了它的心事和感情而发出的歌唱。此外,我们还必须正确掌握《诗经》的价值等等,比如,有人把《诗经》概括为“四家诗”,包括“鲁诗”、“齐诗”、“韩诗”、和“毛“”。
总之,只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,正确掌握学习的方式方法,做到触类旁通,就一定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有人常说理解不了《诗经》,说它晦涩难懂,其实《诗经》就长在你家的院子里,长在乡间地头,是最朴实无华的东西。不需要怎么读,它就在你的身边。
乡里的人都闲不住,无聊时好收拾。收拾家,收拾院,归撂齐整。院里空荡荡的,便期图圆满,这就辟圃,植畦。
除却正经生长蔬菜,偶然也会有些野家伙冒失露头。譬如灰灰菜,马齿苋。人也不去拔,待能凑成一顿时,照样拿来调拌了当菜。
灰灰菜有个诨名儿,藜,史上鼎鼎大名。《诗经》时,便是山野里的一道大餐:“南山有台,北山有莱。”莱即藜。马齿苋虽没登上《诗经》,却也成为杜甫的至爱,“苦苣针如刺,马齿叶亦繁。”这东西吃多了,治胃溃疡。
苦苣这东西也日怪,不往圃里生,就往畦外跑。院里的荫角或砖缝里常有它。若是到了地头,那才叫普遍。但凡能下脚的地方能可能踩着。
不过,乡里的苦苣其实是甜苣。乡里的苦苣叶大齿深,像是锯。若不留神便在嫩肉上划道血痕。
当然,不论甜苦都能填满乡人的肠胃。吃多了,对人生也就看得淡漠了。
这个苦苣在《诗经》里,出现过两个名儿,一个叫“苦”,一个叫荼。“采苦采苦,首阳之下。”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日后见“荼毒”便晓得不知哪个倒霉鬼吃苦头。
诗中提及的荠菜也是满野地里生。不过,这一带乡里多割来喂了牲口,自家倒不明白怎么去做,不像山东地方吃法那么讲究,而且比牛奶还补钙。
儿时,常剥了籽当小鸡,放纸上嘴里唔唔叫,看小鸡哆嗦着走。
和采苦同诗的采葑。其实,大家都经常见,经常吃。号称花心大萝卜的便是。小时候,乡里的农民经常种,靠路边也没人看护。
若是有人路过,看看左右,便拔一根来,也不水洗,也不削,拿牙啃了皮,吃里边的嫩芯。一根萝卜两个色儿,上边白,下边青。
白的不辣,青的辣。现在这种的市场上少了,都一色儿白的水灵。但吃起来,也寡淡无味。过日子,还是有点辛辣,有点淡泊,才有蹦跶劲儿。
蔓菁也是葑,冬天腌咸菜,春天铺纸上晒阳婆,小孩们过上过下,少不得脚踩,但洗洗仍旧扔回去,并且再蒸煮闷放,吃起来,有酸有咸,地道的家乡风味儿,旁处的比不及。
咸酸也是生活本色,少见菜里放糖的。也许是因为平素难得有甜蜜吧。也好,这样人才能真正融入生活。
当然,也有本身便是甜的植物,譬如甜根苗。样子就像槐或刺玫。旧时乡野里到处都是。植株少有过膝的。没在草丛里,在人俯拾当儿看见。一般拔不起,根很深。需要用锹或榔头。
乡里人间起房或填院土,用挖掘机挖,便会露出全部。长有数米,指头粗。我们上学时,过夏,全凭它当家。浸水喝,或嚼来吃。清苦里有浓甜。似乎“苦尽甘来”,叫人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
有的地方也叫甜根苗“大苦”,似乎就是这个意思。《诗经》里的甜根苗,却与苦无半点瓜葛,叫“苓”,“山有榛,隰有苓。”
甜根泡的水金黄,有一种作物,亦开金黄的花儿。乡人常植庭院中,花时赏花,花败后,阴干了,烩或拌凉菜。有个土名儿叫金针,《诗经》里叫“谖”。“焉得谖草?言树之背。”谖即淡忘。
这个淡忘里有许多内涵,譬如让母亲不再担忧在外漂泊的儿女。过去出门在外的儿女都在母亲屋前种金针。
苏东坡、孟郊、白居易、李商隐……金针过去很有名的。可惜如今人却大多淡忘了,只晓得外国有个叫康乃馨的母亲花。不晓得中国自古就有株谖草,郁郁开在《诗经》,开在你家的庭院,滋育过你的肠胃。
《诗经》是先秦的五经之一。传《诗》的到了汉代,剩下齐鲁韩三家,齐人辕固传《齐诗》,鲁人申培公传《鲁诗》,燕人韩婴传《韩诗》,称之为三家诗。西汉的时候,三家诗立于学官,成为显学。这三家都是今文经。同时,毛亨、毛苌也传《毛诗》,属于古文经一派。到了后来,古文经的地位不断上升,齐鲁韩三家诗的地位被《毛诗》所取代。东汉末的郑玄为《毛诗》做笺注,称为“毛诗郑氏笺”。唐代孔颖达做《五经正义》,用的就是毛诗的本子,传注则是毛传和郑笺,这样毛诗的地位就完全确立起来了。
所以我们现在读《诗经》,一般就是读《毛诗》这个系统的传、笺和注疏。怎么读呢?我们以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唐代孔颖达做《毛诗正义》后,成为了读《诗》的最佳课本。我们现在也同样如此,至于本子,可以用阮元校刻的影印本《十三经注疏》。不过这个本子没有标点,需一边读一边句读。当然,现在也有整理过的《毛诗正义》的本子,比如北大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整理本,但是据我所知,这两种都尚且存在着许多问题,但是瑕不掩瑜,给我们读《诗》还是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的。
其次是后人的注疏类著作,朱熹的《诗集传》当然是必读。同时,清人经学大盛,关于《诗经》的研究,可以研读马瑞辰的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、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、胡承拱的《毛诗后笺》等等。今人的著作,也有一些,程俊英先生做过《毛诗译注》,堪称典范,亦可以作参考。